吃烟
2019-2-12 来源: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:次前言
“对于抽烟,我可以说是个内行。打开烟盒,抽出一支,用手指摸一摸,即可知道工艺水平如何。要松紧合度,既不是紧得吸不动,也不是松得跺一跺就空了半截。没有挺硬的烟梗,抽起来不会“放炮”,溅出火星,烧破衣裤。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,就知道是什么香型。若是烤烟型,即应有微甜略酸的自然烟香。最重要的当然是入口、经喉、进肺的感觉。抽烟,一要过瘾,二要绵软。这本来是一对矛盾,但是配方得当,却可以兼顾。”
-----汪曾祺
吃烟
我们这里好多都叫吃,吃烟,吃茶,吃钣,吃苦......结棍一点叫吃生活。我爷爷吃烟,我奶奶吃烟,父亲是四十岁后才吃烟,50多岁后,在我们严重干涉下基于健康原因慢慢戒烟了。我当然也吃烟。烟者,气也,人活一口气。民间有谚:饭后一支烟,做人似神仙。袅袅烟雾中,一切都云消烟散了。活着折折腾腾弄得“烟气”十足,死了烧成灰,化为烟。都是空屁。
好像我从来没觉得奶奶吃烟有啥不妥,早起头,女人吃烟大概自清朝延遗下来的陋俗。穷人家,并不是慕着时尚,如花样年华里的女人弄出些派头来,手一递,腰一掐,自有风情万种;或者是风月场所的女人讨些生计的由头,合着男人的兴致。奶奶吃烟,是得了胃病,止痛,一来两去,就成了习惯。但她不是吃长烟,偶尔吸一下。鸦片抽不起,用香烟来代替。生活的窘迫,习俗的浸染,漫长的等待,一个小脚女人总能在日子的缝隙中找到安慰的替代品。奶奶有时候自己舍不得吃,把别人送给她的烟,积存下来,送给父亲。她也不管有没有变质,发潮,坚定地一支一支、一日一日积累,汇聚成一包又一包。
我最早见到爷爷吃烟,不是纸烟,前头一个铜头,中间是木头,木头和铜头摸的锃骨亮,小辰光,我很喜欢看爷爷抽这种烟(我不知道是不是旱烟),装烟,点火,吸一口,吐出来,非常有仪式感。爷爷这杆枪是走到哪,带到哪,不允许别人碰的。爷爷抽烟时,我会帮他点烟,要花费很多火柴。爷爷舍不得,一般是在烧饭时,伸进灶膛,借助自然点火。我问爷爷,这烟好不好吃。爷爷说,小孩子不要学。但爷爷吃得有滋有味,长长地吸一口,再慢慢地从鼻腔里喷出来,爷爷吃烟,他不吃零食,他把零食都分给我们小孩吃。奶奶吃烟,也吃零食,我喜欢跟着爷爷。趁爷爷不注意,我也偷偷地吸过一口,呛,苦,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难吃的东西了,比中药还难吃。况且这旱烟需要极大的肺活量,小孩子吸一口,根本够不到底。再后来,爷爷改为吃纸烟了,从几分到1角到2角不等的“大铁桥”,“大红鹰”,“大前门”,“雄狮”,“上游”,“五一”,“新安江.”.....过年时节,父亲会敬上几包“古松”、“青松”或者“凤凰”等,那时候的烟都是凭票购买,好烟紧俏的很。对我们小孩来说,最大的兴奋点是可以拿到很多香烟壳,打纸仗(打弹子,打纸仗是我们那个时代小孩的不二游戏)。读小学时,在一些高年级学生的撺掇下,我们也偷偷偷吃大人的烟,我记得以“大铁桥”、“大红鹰”居多,不敢多偷,每次偷一两支,躲到灶披间,或者山岗上吃。实在没什么味,纯粹是图新鲜凑热闹装成熟而已,玩得就是心跳。
我一直认为香烟是苦的,老酒是苦的,生活也是苦的。各种苦倒在一起,酝酿出生活的千般滋味。
?
相比于两老的吃烟,父亲是没有前因,没有后果,硬生生半道杀将出来。父亲在中年之前都没有吃烟的习惯。别人散给他的烟,捏在手里,只是一种手势而已。那种直来直去的烟雾完全是生手的窘姿,与一个正宗的烟民套路相去甚远。年关时节,亲眷朋友到家里来做客,那也是礼节性的客烟。父亲分烟,他自己不吃,或者含在嘴里,自生自灭。后头,父亲走上岸后,做了发网生意,慢慢从被动变为主动,逼着上了“梁山”。“梁山”未上,良民一个,眠床帐子倒是烧了几个洞,在与母亲的有关香烟问题的口角中,父亲的理由冠冕堂皇,振振有词,“我是为了打交道,业务所需,有支烟,闲话好讲多了......”。虽有以公带私之嫌,大头还是站得住脚。烟是市井生活中打开对方大门的钥匙。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递上一支烟,无意间拉近了距离,对方接有话头,不接也有话头,一来两去,言语就有了交集,有了交集办事就找到了突破口。父亲从敬烟到吸烟,终于“堕落”成一个无可救药的烟民。每当有一笔生意谈成,父亲就夹着一条条香烟去孝敬各类老爷。特别是年底,和母亲两个及早打算,进货,排好名单,送烟敬烟,早出晚归。原来,去送人家还这么麻烦,如果把烟送光,父亲进屋时是哼着小曲,耳朵旁夹着烟,如果一天任务没有完成,父亲就阴着脸,躺在床上自己吃闷烟。夹在手指的香烟早已成了长长的烟灰。哥哥和我有时也会从柜子里偷偷地拿一包,这时候烟的档次高了些(记不得了,好像是牡丹,万宝路之类的?),父母会根据对方份量的不同,业务量的多少,搭配好好烟与一般烟的比例。哥哥已帮父亲打理业务,可以名目张胆地带烟,我只能从暗地里下手,反正家里有很多散烟,多一包少一包,他们又不晓得。过年时,父亲高兴会发给我一包,母亲见了不高兴,好样不学,孬样倒来事。父亲呵呵笑笑,装作没听见。哥哥出门时,父亲会关照带上烟,万事有个由头总是好。
香烟对吃烟的人来说是香的,对讨厌的人来说是臭的。母亲说,整个屋子都臭了,连你身子,被子都臭了。有好多次,母亲把父亲骂出去,父亲也不抗争,三十六次走为上策,顺阿溜一样溜到外头去,吃不得耳朵苦,脚还是生在我脚下,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母亲呢?也乐得眼不见,鼻不闻为净,俩人各自达到目的,内部矛盾自我解决。一般来说,父亲这时肯定在小店,或者船长家里,谈天,散烟,吃烟,这种场面我能想像得出,人群涌在一起,海阔天空,胡天胡地,海里的人从来没有细声细语概念,在船里机器声喂养大的声音,即使在陆上,也同样应着同一分贝。讲个屁大的事,讲着讲着,屋外,马路上都能听得见了。散尽回家,解了瘾头,父亲会轻手轻脚上楼,好像做了亏心事,如这时母亲差个懒,他会百依百顺,捏了男人的短,办事方便多了,绝对是经验之谈。
一个合格的烟民,是无事无刻都会想着烟,念着烟。父亲深陷在烟民的泥河潭里不可收拾。逐渐从交际发展到自己买。那时财经大权掌握在母亲手里,父亲就向母亲讨钱,或者把零落在柜子里碎钱,聚集起来,一趟一趟往小店里跑,父亲有个习惯,空闲时,不喜欢在家里呆着,总是寻个理由往外面跑,所以,他买个烟,从来不买整条,一包一包买。吃完了,就找个理由买烟去。这让我想起,多年以前,我工作期间,一次集中阅卷时,一个老师为了少批几叠试卷,竟然跑到老远的街面去买烟,一来一去,就一个小时,组长问他,他回答,旁边小店这种烟没有了。一个套路。
?
烟民的标配是手指焦黄,面孔发黄,牙齿发黑发黄。身上有股怪怪的味道。男人两样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有,一是烟或酒,二是足球,看或玩。五毒俱全是真本事,可以笑傲江湖了。正常人需要二三毒来装点。李渔说,人无癖,不足交。要不歌里怎么唱:“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,不知道它们跑哪里去了,我怀念你的笑,怀念你的外套,还有你身上淡淡的烟草味....."。一个烟草味的男人是很有魅力的。吃烟的味道来自哪里?是面对一包簇新的香烟,开包拆封,扑扑手指弹几下,跳出一根烟,两指富有粘性地弹起来,凑到嘴里,点烟,呼得一口。经嘴入喉返肺,再是原路返回,经过鼻腔,吐出两股,洗心洗肺,荡气回肠。这一时刻,做人达到了顶峰了。伟大的老人家说过,烟是好东西。它跑路,洗脑,静心,自明朝以来,烟伴随着我们走入新时代,有很多伟大的决策,在烟雾缭绕中一烟定天下。
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这样的时刻?
当别人在公开场合把烟分给你时,意味着你已长大成人了。或者说你以获得长辈认可的身份。有一年,我去外婆家拜岁,舅舅们开始不把我当小孩看,分给我一支烟。那年我刚工作,其实,我口袋里揣着一包烟((想证明自己是成人了)。几次想敬,心里没底。只敢在同辈人之间流转。现在,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掏出香烟,加入吸烟的队伍,吞去驾雾。这个时候,母亲是不会说我的。笑而不语,瞥来一束嘉许的目光。撑了面子。诗酒趁年华,我在最好的时光里,赶上了烟的年华。
烟民表现形态各一。“烟道"也各显神通。办公室是正派吃法,程序到位。你一支我一支讲究分寸。茶室讲究情调,不至吃相难看。寝室则是随便多了,放松宽心,质量好坏不论。聚会是摆在台面上的市井生活的反映。衣着光鲜,揣着好货登场。张三,李四,王五,一一入座,招呼寒暄,场面上蜻蜓点水一过,掏出一包烟,打上一圈,啪嗒放在桌上,上面安着打火机,这时是不好把香烟掖在袋皮里。小拘俚气上不了台面。常言道,“烟酒不分家”,接着各种吃相陆续登场,特别是三巡过后,话题放开,动作奔放,“烟姿”万千,即使你平常不吃烟,一阵兄弟长兄弟短的忽悠之下,捺不住叼上一根,遂了劝者心愿,不吃烟者的有个好处,只需嘴里一衔,别人会帮你点烟,享受了尊者待遇。而劝人者也心满意足,终于有人“入水”了。喝高的,喝低的,激动的,感伤的,骂娘的,颂德的......一应俱全,烟酒销得万古愁啊。如果有一女士拉下水,那这餐饭是色香味三碰头,笔力有限,无力展开(此处容你真空)。若说,最见风采还属麻将桌上,民国才子徐志摩有一句: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塌,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。我以为对也不尽对,单说这烧烟必是达到了极致,抽烟的人开始吞云吐雾。牌顺时,就把香烟兜一圈;牌不顺时,就烧霉气一支接一支的抽。小小一间麻将馆内,被烟雾包围。即使有女士用手挥几下,想驱散一下眼前的袅袅青烟,也无济于事。每个人都是一支大大的“肉烟”。据我所知,在麻将桌上,敬烟好像不太时作了,风头好时,怕分走运气,风头不好时,更是顾不着了,连一只打火机也要死死扣在自己的面前,自己的火是不允许别人来烧的。当然这又是一本书的内容,实在写不过来。
年代初,买包好烟,需人民币七八十元,寒假过后我的一个同事,总会带来几包软中华,他说,过年了,香烟要吃好,交关有派头。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,没承想他的这一举动还影响了我。做人的气场,甭管袋皮里有没有钞票,相中的东西,弄了再说。说到底这也是一种地域文化,海岛人的气场在这时在浮现出来,说说岛城的两个地方,早些年,S城与D城,S城的后生小歪到舞厅白相,如袋皮里只有元钱,必定买包软壳中华,掼在茶几上,架起脚,一幅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洒脱。D城呢,也不能说全部,要了一杯白开水,连门票钱也要逃。若是带了女伴,装了客气,买样零食,问问其问问其,倒是合了农家子弟勤俭持家的本色。吾乡方言讲,耍管堂一样。
我第一次见到年青女子吃烟,还是吃了一惊。绿岛舞厅的音乐蓬嚓嚓蓬嚓嚓地响着,隔壁东道主学校的一个老师,见到我们,热情地招呼我们去包厢里坐一会,推开门,朦胧中抬眼望见一个女子,靠在椅上混在一堆男人中,安恰地吃着烟,她穿着皮大衣,戴着眼镜,一幅斯文的样子。看见我们也不避嫌,细长的手指勾着,微微一笑,算是打了个招呼。我突然遇到这个阵势,吃了一慌,怔住了,一时三刻脑子打结。那时的我,是全然不能接受一个年青女子的这个做派。
这是愣头青的往事和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岛青年固有的成见,现在不会有这种想法了。翻翻旧报纸,上海的阿飞,老早已粉墨登场了。小岛市面的闭塞可见一斑。自此后,床柜旁梦露的那张海报张扬起膨胀青春的一个个旖旎眩目的梦。
歌里唱道:我的青春像鸟一样飞走了。我很怀恋教书那段辰光,老王吐出的十八只烟圈,小叶同志一只只叠起一溜高高的香烟壳,牌子什么的我已忘了,很有意思,他每抽完一包烟,把空壳子留置,在办公桌上一只只叠上去,一排又一排,他那时,长发飘飘,长住寝室,还有孙、后来的袁等,我们一起度过了最好的青春。谢谢侬,美好的东剑中学时光。青春没了,学校没了,他们也都戒烟了。
而我却成了一个地道的烟民。我曾写过篇不成样子的小文《遗忘的方式》,记录着一段心路历程,说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,有点矫情了,滚滚红尘,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,你无法把握,你深陷其中,说不清好与不好。在时代的潮流中被裹挟,理想已死,全都是梦一场。
至于我如何成为一个烟民,实在无趣得很,不说也罢。需要澄清一点,这与我曾经从事的工作性质无关,只不过叼根烟,在漫漫长夜加班像是有个人做了伴。上山容易,下山却难了。
只有在戒烟的时候,才知道烟的厉害。我无数次想过戒烟,也好多次付诸于行动,也曾在亲眷朋友面前信誓旦旦地发出宣言,老婆大人更是开出极为慷慨条件:只要你能戒烟,你买什么做什么都行!这已达到了极致。最终都不了了之。非我意志不坚定,实在那烟诱惑太大了。当你与一种相交已久的习惯诀别之后,又找不到可更新并保持注意力的习惯时,最容易出现的便是反弹。最厉害的一次是,我戒烟两星期后,突然像失了魂魄了样,干什么特没劲,生理、心理全不对劲了,心里涌动的想法出来,就吸一口,吸一口再不吃了。这一口,就要了你的命,“死灰复燃”。前几年,一部热播的电视剧《人民的民义》,祁同伟与高小琴在喝茶聊天时,在谈论侯亮平时说了一句话:一个男人能把烟戒了,他对自己得多恨啊。我没有戒烟成功,是否可以说我是个善良的人,对自己不够狠。可转念一想,干吗要这样吗?烟酒人生,我不会喝酒,那就保留一样,能抽就抽吧。杭州一个寺里有幅门联:“是命也是运也,缓缓而行;为名乎为利乎,坐坐再去。忙忙人生,坐下来干啥,坐下来吃烟“。想想蛮好,我也就心安理得了。“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?”我也在林语堂先生的文字里找到依据,“因为经过此次的教训,我已十分明白,无端戒烟断绝我们灵魂的清福,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”。
尽管这样,现在对吃烟的环境越来越不利了,各东各处写着禁止吃烟,开会不能抽,飞机上不能抽了,国外很多地方不能抽。所以你才特别珍惜从会场上出来,从飞机上下来的第一口烟,这一口,真真是“与尔销得万古愁”。再不定,哪一天,什么地方都不能抽了,这日子算起来很可怕,算算过的日子,当然要珍惜了。
关于吃烟水平,汪曾祺先生有一段精彩文字,特意录下来,作为结尾。
“对于抽烟,我可以说是个内行。打开烟盒,抽出一支,用手指摸一摸,即可知道工艺水平如何。要松紧合度,既不是紧得吸不动,也不是松得跺一跺就空了半截。没有挺硬的烟梗,抽起来不会“放炮”,溅出火星,烧破衣裤。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,就知道是什么香型。若是烤烟型,即应有微甜略酸的自然烟香。最重要的当然是入口、经喉、进肺的感觉。抽烟,一要过瘾,二要绵软。这本来是一对矛盾,但是配方得当,却可以兼顾。”
他老人家,可算是吃烟得道了。吾与之相比,简直是泰山与磨心山的差距,余生,或许更应磨之。
古岸
生于年代
浙江舟山人
低调做人,安静生活
古岸赞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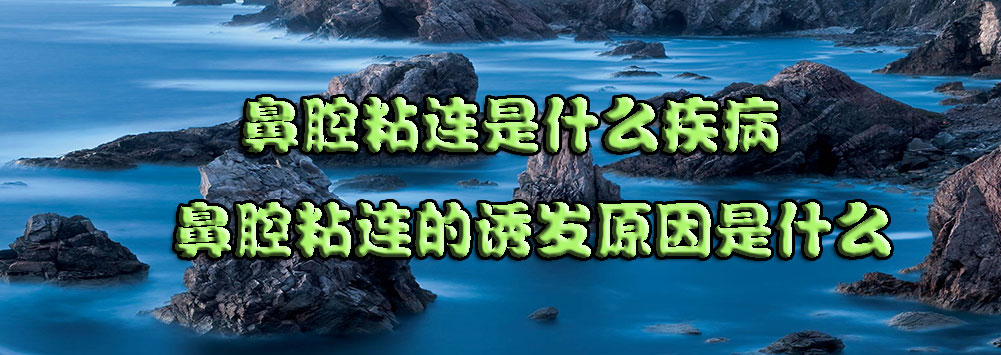
 健康热线:
健康热线: